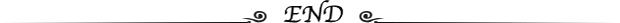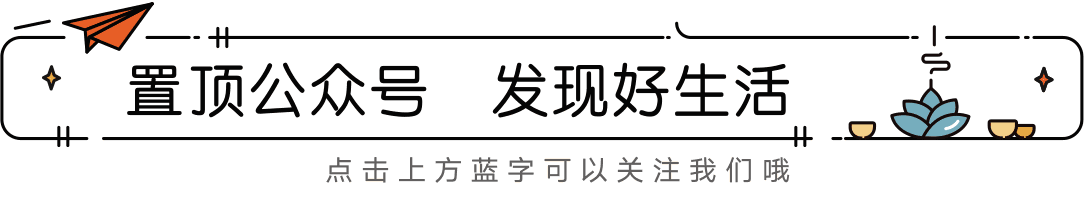
陇先生——居甘肃,评甘肃,兴甘肃!敢说,敢做,敢为...数万人订阅的专属于甘肃人的微信大号。点击标题下蓝字“陇先生”免费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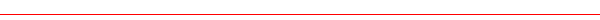
核心提示:故乡,在汉语词典中指一个人出生地或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但在现实生活中,故乡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故乡。
常言道,月是故乡明,水是家山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典型的小农文化。然而,不仅仅在兰州,在国内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因为生活却只能从城市怅望家园,他们不可能回去,也无法回去,即使回到故乡,也看不到故乡以前的影子。
中国的农耕文化导致内向型的文化形态,也就是保守型的一种心理,没有侵略性,或者说没有外向型。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人们对故乡的概念越模糊,越落后的地方,人们越不愿意离开土地。
而现在,在城市和乡村夹缝里生活的这群人他们缘何不回去,回不去呢?于是,本报记者历时半月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记者调查:他们缘何不愿意回故乡去
采访中,武山县城关镇干部韩亮说,有一次他周末带上小学的女儿回乡下老家看父母,他城里的媳妇非常不乐意去,原因很简单,就是农村生活很落后!
对在县城生活了10多年的他说,在农村,遇到大雨天气,地面湿漉漉的到处是泥水,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到一段路程,两个裤腿上几乎全是泥巴。住宿吃饭的不习惯就更不用多说了。
今年32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回老家也是他最开心的事。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农村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在故乡之外,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飞速上涨,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包括从他所在县城到省城的大巴车也在提速。但是,对于故乡所在的那个西北小镇,似乎还是他刚参加工作时的样子,变化一点也不大。
著名文学评论家杨光祖教授的老家在甘肃通渭。杨教授对记者说,他对故乡几乎没有多大的感情。1989年,他从老家出来到兰州求学,那时候似乎就没有多浓厚的故乡感情。不过他现在还是要回故乡的,因为那里有他的亲人。
后来,随着他爷爷奶奶的去世,他感觉自己与那个小山村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他说,在农耕文化里,没有个人,也没有平等,其实是很势利,有时候只是表现得不明显而已。农村人为什么看重官,是因为日子过得穷,因为日子穷,所以才势利。现在,他几乎很少再回故乡去了。
即使他有事情回去,感受最深的还是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
据记者了解,甘肃作家人邻每年都抽出很多时间深入甘肃部分乡村考察采风,他曾写过《岷州札记》等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在他眼里,民间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他对自己常说一定要深入农村,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更有味道。
不过从他写的《上坟记》中,记者能深切的感受到他的无奈和失望,那就是故乡在一天一天的沦陷。 记者在武山龙台沟门村采访时,该乡乡镇干部关飞告诉记者,这个村子里年轻劳动力都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根本原因是当地农民觉得种地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划算,一个不大的村庄里留下来的多半是老人和小孩。
所以,当你看村庄沧桑落后的样子很是让人心寒。从龙台乡沟门村到县城一天只有2趟公交车,该乡街道上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饭馆和招待所。平时人们赶集办事也要跑到10公里外的滩歌镇去,村民们舍不得花5元钱拼车坐小面的车,一般都是10多个人挤在三马子上往返。
特别是冬天,山路上积了厚厚的雪,车祸时有发生,非常危险。这也算很多外出打工者不愿回农村创业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杨光祖教授打趣说,他现对自己的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在甘肃很多农村,民风已经不是很淳朴了……。
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 我国著名作家梁鸿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出版后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不难看出,故乡是被一部分栖居于城市的人抛弃了的,而不是故乡抛弃了这些人。
旅游式打工:充满无奈和尴尬的人生经历
从记者采访的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看,一说起在异乡漂泊打工的生活,他们似乎聊得最多的还是谁在外面挣了不少钱,谁在外面出了事。在兰州这个省会城市,他们一有聚会见面的机会,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会落进故乡里,全都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情,张家长李家短的,还有童年时代留在故乡的回忆!
吴元华,湖北十堰人,今年43岁,在兰州打工已经10年了。他说,他去年干活挣的13000元老板还没给他,过了春节到现在,他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红泥沟租了间民房一直在等着要工钱。
他告诉记者,其实他在兰州生活过得并不好,他一年辛苦挣来的钱刚好够一家四口人平时的生活开销,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但真正让他们回老家去,他还是不想再回去。
在记者到吴元华租住的院子里采访时,记者看到一群来自陇南武都的农民工正在聊天。谈论家乡的事情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的意义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东西。 回去做啥呢?没钱也没希望。
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当一个人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心的时候,我会回到我的老家去蹲个十天半月的。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我就再回来。而在平时,她几乎不回故乡。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供职的刘姗姗说。
刘姗姗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兰州。这是一种十分深刻的无奈。 来自陇南乡村的张筱,在兰州已“漂荡”了十多年,现在兰州玛雅广告公司供职,有固定的工作、收入也还不错。
他说与其他同年代、经历与他相似的一些农民工相比,他还算是幸运的。做为一位抛离黄土地多年的“农民”,他的历阅虽不精彩,但不可谓不丰富:在最基层乡镇工作过、也在乡镇企业供过职,最终他的落脚点选在了省城。
用他的话说,离开乡村是因为生活所迫。他说最终他还是要回老家去的,他融入不到这个城市,他的根不在这个城市。虽然张筱工作是在写字楼里、生活在省城,但他的心依然是属于乡土的。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记者的朋友朱辅国先生说,人永远都会有故乡情结,只是大与小、出生地意义上的和心中的故乡的区别。
我的老家现在越来越物质化,同时代的朋友虽然和我之间保持着亲情般的友谊,但价值观背离太远,老家是回不去了。故乡是一种心理认同,你的眼界越宽,了解越多,你的认同越具普世价值,你的故乡就越大。
别处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都失去了心底的故乡
28岁的于小强是青海皇源县人,他现在在兰州东岗一家货运部里当搬运工。上周末,按照事先的约定记者前去采访了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木板支起来的单人床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包包菜,土豆和面条。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里面全是他的衣服。
“整个房间十分简陋,感觉是临时的,特别寒酸。”他告诉记者,一天忙下来,累的骨头都要散架,他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在手机上听听广播,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整整4年,很少回老家。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于小强说,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兰州,等赚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和娶媳妇。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漆小妹的老家在天水农村,初中毕业后,她到兰州来打工,先在饭馆里当服务员,后来自己在临夏开了婚庆公司,她时不时跑到兰州来办事。她说,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
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故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
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嘈杂,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刘晓霞是四川绵阳人,2008年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留在兰州一家报社当编辑,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
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刘晓霞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作家张筱已是人到中年,他从不以农民身份为耻,也不用农民的身份炒作。他和记者在关于乡土与漂泊的对话中,他谈到了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背景下乡村的无奈。张筱还谈到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那本书,说书中剖析的土地归属权问题,才真正是农村贫穷落后的原因。
而谓“失地农民”,根本就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拥有过自已的土地,如何失去? “只有真正在农村生活的人,才深知农民的艰难。
而农民是没有自已的话语权的,比如现在一些乡村在推广某项特色种植产业或进行某项农技推广时,必然要规划连片种植,但规划进去的部分农户又不愿这样搞,最后的结果是通过行政命令,硬性搞、一刀切。农民都称这样的‘推广’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山村,十年后的今天,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出了几名大学生,也许这些大学生中个别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但乡村贫困的窘境没改变。
张筱坦言,他最初到城市谋生的愿望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供养孩子完成学业。这个愿望,不是个案,很具有代表性。谈到就业问题时,张筱说农村的学生自考上大学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回不到故乡,因为这名学生的户籍从这一天起已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人口”。
许多毕业后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农村青年,由于户籍的变动、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很难再回到农村。如果说进城打工的农民是“盲流”的话,那么这些人,已形成了城市新的“盲流”。
中国新闻周刊一位记者曾在2012年4期的《读者》杂志撰文说,他在采访时看到,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
有的地方村民都住进了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民居,然而那些突然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
“一提起故乡,她首先想到的是该县石磊街口的一棵大槐树。有几十米高,不仅给了她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那个县城的发展变迁史,而当她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走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
兰州工作的赵芳芳是陇南宕昌人,在记者采访时她说,她的故乡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清明回乡,她发现县城老街上的那棵槐树生长情况不太乐观。她说,如果没有了树,土地也就会失去灵魂。
精神的故乡:沦陷之后的出路又在何方
2012年3月31日下午,记者在安宁某高校采访了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杨光祖教授。当记者和他谈起了边缘人与故乡的话题时他说:在他看来,做个边缘人其实是很好的。
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是边缘的,一进入中心,就出问题。钱钟书也说,学问一成显学,即为俗学。但如农民工这样的边缘人,国家必须要尊重、爱护。爱护这样的边缘人,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
作为农民工来说,其实,这种身份也有它的好处,让他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的另一面。所以,往往那些农民工比我们的很多学者,要目光敏锐。 说到家乡,他倒没有什么家乡情结。
他本人对“家乡”比较反感。他认为,中国的农耕文化,讲究落叶归根,月是故乡明。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观念,甘肃的很多企业走不出去省界,中国的很多企业走不出国门,也有这种故乡情结的潜意识在作祟。到现在,我们的国人仍然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是到21世纪才产生的。
西方人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么浓厚的家乡情结,西方的传教士,他们能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播到中国最偏僻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老死,这是我们的文化所做不到的。我们无法把儒家文化传播到欧洲,甚至全世界。就是因为没有“人”传播。
谁都知道,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天生有着好奇、探险的精神,一直从古希腊,越过两伊、阿富汗,到达印度。这是我中华民族无法做到的,我们只是把入侵者赶出大陆就可以了,从来不会到别人的地盘看看,更不会越过海洋。海洋,永远是中国的最边际。
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向型是没有创造力的,这对个人、民族的发展来说是绊脚石。现在看来,故乡观念是非常落后的一种观念,不具备现代意识。
对话中,杨教授告诉记者,西方有位作家他现在想不起名字了,那位作家在一篇文字中曾这样说,一个认为自己的家园甜美的人还是一个脆嫩的初学者;一个把每一片土地都当作祖国的人是强壮的;但只有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域的人才是完美的。这个话很值得玩味,到现在他都在思考第三句话的含义。
他现在觉得兰州是他的第二故乡,这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给了他很多东西,比如自由,文化,个人、超越。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兰州了,他在老家生活了20年,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工作了23个年头了。
杨教授幽默的说,“作为文化人,我还是喜欢做边缘人。”在他看来,世界上很多文学大师都是边缘人。中国古代的孔子,朱熹,现代的鲁迅等哪个不是边缘人呢?
文化人要甘于边缘,才是一种好的状态。如果高尔基不是边缘人的话,你想他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即便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其实也一直在边缘自己,他也是一个边缘人。
对于故乡情结,倒没有必要那么浓,我们要超越那种小农文化,但民族的优秀文化一定要传承。文化在那里,故乡就在那里。就像汉字到了那里,那里就有中国文化,有汉字的地方也可以说都是我们的故乡。
扩散出去
让更多朋友看到!

点击右下角“写留言”跟陇先生进行互动吧!

欢迎转载或分享到朋友圈,转载请注明来源。